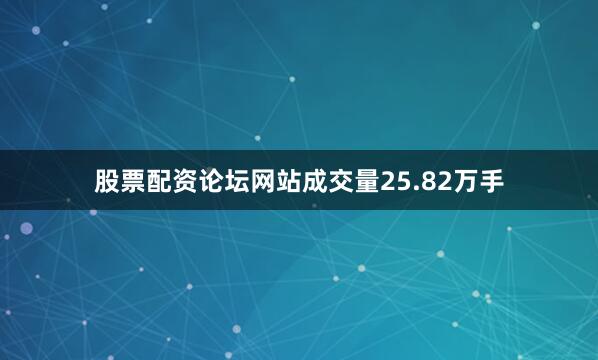何为中国?从当下的表现看,中国就是唯一对西方实现赶超的国家,而且用的是中国模式,官方将其称之为“中国式现代化”。
没错,这的确可以代表中国,但这是实践和行为,要回答何为中国,就需要更进一步,解释为何中国能成为能够实现该超西方的唯一国家,说明白“中国式”现代化的“中国式”就是是什么。
其实中国模式的起点在鸦战之后的晚清,当时的设想是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、“中体西用”,这既是中国模式的初心,也是对中国模式的最后概括。从那时,到当下,180余年,中国一直在这个框架内发展,直至最终成功实现对西方的反超。目前中国的工业能力比G7的总和还多,完全碾压西方,军事技术也已经系统性地领先美国。
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也好,“中体西用”也罢,其核心要义在于,在坚守文化独立的前提下,以中国自身文化为主体,学习和引入西方先进技术,然后实现反超,再去教化、同化西方蛮夷(制夷)。
也就是说,中国模式,是有体、用两重要素构成:中国传统文化是其体,所以引入的西方技术是其用。但是,在当前的主流学术界,却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,只知从西方引入的技术之用,却不知所继承的中国固有文化之体。
主流学术界的研究也是聚焦在西方之用上,而完全无视和忽略了中国之体。原因很简单,当前的学术体系,是在范式上是西化的,在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所引入和建立。而中国文化核心要素,在西方并不存在,也落在在西方学术体系的认知和研究能力之外。
因此,当前的学术界,是没有能力真正理解和认知中国模式的,没有能力真正理解当下的中国的。
何为体,何谓用?体就是活的主体、主导者,用就是死的被利用的被主导者。体是目的,用则是工具。所谓的活的,就是具备独立的思考能力,能够独立地思考,包括判断、选择,然后去指导决定行动。所谓死的,就是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,不会去判断和选择,而只是思考对象,是判断和选择对象。
以科学为核心的现代西方学术体系,只有用,而没有体,是用学,而非体学。其研究的对象都是死的物,即便是研究社会,研究人,也是当成死的物。研究的目的就是发现规律、真理。所谓的规律、真理就是死的物所会永恒保持的状态。规律、真理本身就是死的,也是死物的典型特征。
真正的人是会独立思考的,而思考的核心特征是应变、变化,而不会固守什么规律和真理。一切的被认为规律和真理的东西,也都不过是思考对象。真正的独立思考是要打破一切的成见的束缚和制约,所以孔子说“勿意、勿必、勿固、勿我”。
“勿必”就是不要认为什么是一定的,与规律、真理概念截然相反,客观规律、真理就是最大的必。
为何现代西方科学以死物为研究对象,并且以孔子所极力反对的大“必”为研究目标,甚至最高追求,根源在现代西方文明并没有实现和学会真正的独立思考,缺失真正的独立思考能力。因此,他们的学术体系就不是以独立的思考能力为研究对象,不是以如何保障独立思考为研究目标和最高追求。
独立的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体,西方文明中压根不存在这个概念。也就是说西方文明是无体的,这导致其学术体系的无体。
在甲午战争之后的清朝的临终时刻,出现了“中体西用”的概念,同时也出现了反对的声音,其代表人物就是严复。他认为,这会阻碍中国对西方技术的学习和引入。其理由是,中国有中国之体,中国之用,西方也有西方之体西方之用,而体用是相配套的,西方之用可能不适合中国之体。
他还举例说,牛有牛之体用,马有马之体用。不能将马之用强行安装在牛之体上。
严复在很小时就学西学,然后被清廷公派留英,所以精于西学,而疏于中学。这导致他压根就没能理解体用的概念,不知体位何物。体不仅只有人才有,而且只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。体就是思考能力本身,也就是人心、心性。
所以,不仅牛马没有体,西方也是无体的。
中国的传统学术恰恰重体而轻用,是以体为核心的,以义理和心性为核心。这就是以五经为核心的经学体系。
义理、人心、独立思考能力,三者实则是三位一体的:实为一个东西,只是维度不同、侧面不同。思考能力是从功能上说,人心是从主体上说,义理是从属性和表现上说。
在中国文明的初创期,中国的古人就发现,人会思考,具备思考能力,于是就将思考功能独立出来,而且将其作为人的本质。然后给思考功能起了名称,叫“心”。“性”就是人心的属性、思考功能的基本属性。
所谓思考功能的属性,就是人在做判断和选择时,所以依据的标准,而这些标准是内在的、天生的:“善善,恶恶”。善善,就是以善为善,并且偏爱善;恶恶,就是以恶为恶,并且厌恶恶。以善为善,就是能够判断善、辨识善。偏爱善,就会选择善。以恶为恶,就是能够判断辨识恶。厌恶恶,就是拒斥恶。
人的所以天然具备的善恶是非标准,就是人心的属性,思考的属性,人心是依据和遵循其属性去思考,去判断、选择和行动的。如果遵循和顺应其人心的自身属性,一个人最终的行为也一定是善的,而非恶的,一定是合乎义理的。因此,义理就是人心属性的在行动上的表现,也是其人心的外化。
这也是孟子性善说的核心要义。
中国传统的思考,是基于扎根于现实,扎根于人间人伦,而非西方式的脱离现实的冥思。西方的冥思起源于神学,冥思的对象是神灵。后来哲学和科学尽管有去神学的成分,但都没有完全摆脱其神学窠臼。所以康德以仰望星空为高,牛顿的思考也是被从上面掉下来的苹果而起。
所以,中国式思考的目的也是为了实践、行动。而西方的冥思、思考则是排斥实践的,即便到了现代科学时期,也是如此。所以,马克思才会批评道,他之前的哲学家都是为了认识世界,他则是要改造世界。
其实马克思也没有完全说对,他之前的哲学家并非为了认识世界,而是为了认识神灵。而在他之后,西方的哲学和科学也并未完全挣脱此种神学属性,包括他自身的学问,所以中国才主张“理论联系实际”、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”。苏联就不懂这些,所以它最终解体了,老马的那一套也被完全抛弃。
义理、心性、思考能力,都是抽象概念,看不到、摸不着,是不可直接认知的。看得到、摸的着,可以直接认知的,是人的实践行动。
因此,要学习认知义理、心性,要维护人的心性独立、思考独立,其方法只能是通过已经发生的行动。已经发生的行动就是历史,历史有两次含义,一个是历史本身,是一个是对历史的记录。我们只能通过对历史的记录去学习历史。
五经不仅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记录,而且是文明早期阶段的,历史跨度很大,从文明初创的伏羲时代,直至春秋时期。
不读五经,就不足以知道何谓义理,何谓心性,何谓独立思考,就不会知晓中国文化之体。对中体西用的中国模式,也只能知其一半,而且是次要的一面:知用而不知体。
炒股配资炒股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云南配资平台麦芽是更为合适的选择
- 下一篇:没有了